不道德(十九1-11)(续)
(六)
我们对于第十九章开头的场面的话,要准确而又慎重,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容易以为它所说的是关于非人性的不道德,而惩罚乃是施于任何容许它存在的社会。
这段经文出现‘鸡奸’一字,即表示男子间的同性恋行为。我们无须过于深入地探讨它是不是叙述所多玛整城男子,对两个无辜陌生人一致的性攻击。不论老幼都围绕罗得的房子,要求‘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译注:中文和合本未照英文圣经译出‘同房’(Know),同房平常是用作性的含义,参看创四1,17;卅八26)。无疑,我们是需要把‘天使’想象作青春年少而又姿首俊美,引起那本已深受恶习惯玷污了的市民的情欲。但是所多玛人的野蛮刻薄和他们的表现作法应同受定罪。
说故事的人似乎选择了‘鸡奸’作为所多玛的邪恶的一个例子,并不打算以它为后来被毁灭的惟一或主要原因。反对它与它的邻邦的‘呼声’,不止这一项的罪,还有多得多。如果我们查考创世记中这个故事其他的暗示,便可以证实。只有犹大书(犹7)提出所多玛的‘逆性的情欲’是显著的事。反之,耶稣却专注这场面中的其他主要特点,那就是所多玛的泠漠:‘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太十14,15)以西结(或许想及十三章中罗得拣了‘最好的’地区,这拣选使他到所多玛去)更把这情景推广开去。‘他和他的众女(那就是蛾摩拉与平原的其他城市)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们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结十六49,50)
(七)
所以我要提出,如果我们只用道意义解释他们邪恶的性行为,而忽视他们更广泛的邪恶,我们便没有见到 神对平原众城市审判的充份理由。我们攻击‘同性恋解放’和我们时代其他的同性恋之言论之出发点尤其应该如此。
毫无疑问的,在旧约,同性恋是‘可憎的事’,而且与乱伦、通奸、献婴儿祭,和兽奸完全定为当死的。参看利未记十八、二十章。利二十章还加上交鬼的、行巫术的,和咒父母的。‘在这一切的事上’,列邦‘玷污了自己’(利十八24)。这些行为使民族不配‘归耶和华为圣’(利二十26)。
作为基督徒,在有关伦理的事上,我们应当依循新约而不是旧约。我们必须老实地承认,在这些事(正如在有关对待其他种族与民族的意见)上,旧约通常是排他主义的,也是残暴的,很难称为基督徒应持守的。正确的意见,是不论其作法多么邪恶和讨厌,都应先考虑法律的规定。尤其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耶稣在法利赛人把那个在行淫中抓到的妇人带到祂面前时(也要记得,照利未记应定死罪)说的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约八7)。这一点也不是说耶稣赦免奸淫,虽然祂对那妇人说:‘我也不定妳的罪’。它的意思是祂嫌恶非难别人。祂实际上是在作我们刚才引述的先知以西结所作的。以西结不是对所多玛宽大,但是在结十六章的晓谕中,他的主要目的是责备耶路撒冷背弃信仰,这在他看来比所多玛所行的还坏。所以在约翰福音八章耶稣扩大了罪恶的范围,包括表面上的善和明显的恶。惟有祂是言行一致而且确实这样作。在旧约中,就连以西结书十六章那段,也难以使它本身免于虚张声势与有自高自傲的气味。
对于道德问题,如同性恋或关于奸淫,随时随地都有争辩。没有一个社会能以逃避对这些问题的决定,而基督徒也像其他的人一样,有权听听他们的意见。我是确信他们应当比现在所作的更坚决地反对现代社会引进来的自由;而我也不怕大声疾呼,我盼望他们运用新约作武器而非旧约。
但是当我们研究创世记十九章的时候,这却既非其时,亦非其地。它的主题是泛论人类的罪和 神对它的反应,而不是这个社会或某一特殊社会的健康问题。它所攻击的是那些不论断自己,而只论断他人的人。所多玛和蛾摩拉并非只是世界上另外两个全然邪恶的城市。他们就是我们自己和一切‘文明’人,直至现在我们都厚颜无耻地愚弄 神一切律法,以致祂降下我们应得的报应。除非我们明白这意思,而且以此为这故事的必然结果,否则我们便绝不能超出它以外(正如我们回忆在上章中亚伯拉罕未完的代求所要求我们去作的)了解 神的怜悯与慈爱。
推诿(十九12-23)(续)
(八)
不过,创世记十九章不只关及所多玛和蛾摩拉,也关及罗得,他与亚伯拉罕同闻 神的呼召,后来却冷眼拒绝了,而且来到所多玛寻求比较舒适的生活。他被四王的军队掳去时,得亚伯拉罕的营救之后,又选择了回到那里。如今他在城市生活中安定下来,成了一些物业的拥有人,结婚,生了两个女儿,而且她们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
在本章最后我们所得到的,关于他人格的崩溃的写照。所呈现出来的,他并不是个坏人。实际上,在故事的开始,他仍然是敢作敢为而且慈祥的。但是到末了,虽然他逃过了大变革,他却显露出他是衰弱可怜的人物。
故事开始,当个陌生人临到时,他正坐在所多玛的城门。他所受的游牧教育大露锋芒,他邀请他们进他的房子里度宿。他对他们的所知,不过如亚伯拉罕在希伯仑一样。但是他了解所多玛人,当陌生人礼貌地婉拒他的邀请,并且说要在街上过夜时,他便惊骇,坚决地要他们与他一同回家去。他为他们的安全的恐惧,完全证明为合理,因为不久之后,一群淫乱的暴民便在他的门前喧闹。虽或有点鲁莽,他却是奋勇保卫他的客人。他出去对那群暴民提出,只要他们不伤害这两个年青人,他将给他们他的女儿。这点对我们,不免觉得过份热心;似有不可饶恕的残忍。但是希伯来听众却不会这样想。罗得既然自己负起款客的责任,他便必须贯彻到底了,不惜冒他自己和他家人的危险。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们是到了他的家。对此,听众会认可便是证明。
暴民对罗得的勇敢的反应,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感到,这个外族人我们宽大地让他们住在我们当中,他们怎么有权论断我们,而且提出给我们女子而不是男子呢?作为移民,他应当入境问俗,而不是当面夸示他们自己。我们要给他好好的教训一顿。
说故事者在这段中精明地撮述所多玛的堕落,他显然是期望引起我们对罗得一方的同情心。他选择住在所多玛,但他在那里却并不开心,也不受欢迎。在他心里仍然是亚伯拉罕的侄儿,而他也有游牧民的道德心,他仍有希望。
(九)
这两个天使,他们来访所多玛主要的目的,乃是要察看那反对它的‘喊声’是否属实(参看十八21),现在完全相信它当受毁灭了,而作为对于将要来临事故的预尝,他们便使那些在罗得屋子周围的暴民都瞎了眼(译者注:中文和合本只译作‘昏迷’)。不要以为这是永久性的瞎眼,只是一些类似保罗在大马色途中的情形(徒九3-9),就是在神性威严面前的瘫痪;不过在这场合,那受罚者乃是不同的一种人罢了。
天使们的行动对罗得也是一个转折点。当他们行动的时候,他一定在拚命猜想他们是谁;而当他们把他从他血气之勇所引致的后果中救援出来时,则真像大白。或者作者在暗示,他仓皇去护卫他们时,实在是他们在护卫他。有些像亚历山大朴帕(译注:Alexandar Pope 1688──1744英国诗人)所描写的‘怕天使走错地方’的‘愚夫’。
总之,他俩现在公然宣布他们为甚么而来,并且恳切地劝告罗得和他的家人及时逃走。但罗得再一次不能贯彻他的始终。他毫无悔意地露出了他的本色。他对于天使们告诉他的,感到震惊和印象深刻;此时他确知他们是从他曾一度敬拜过的 神而来的。因此他催促他的亲属马上逃走。但是当他的未婚女婿们对他发笑,以他为戏言时,他的决心又消失了,当夜没有任何行动。摊牌的时候,他仍然宁取所多玛而不取 神。他在那里建立起他的新家,他的家人在那里,虽然圣经未明说,却意味着已拥有以西结所谓‘过量的食物和相当兴旺’。他的未来女婿当然对,无须惊惶。
第二天早上,他的最后机会来了。但是却如作者所说的,他仍然‘迟延’。事实上天使要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和他女儿们的手离开那城。甚至到了此时的罗得还在推搪。他求天使不毁灭那‘又小又近的城’,而容许他在那里安定下来,而不要逃到在流浪时期住过的山上去。正如本仁的到处探听丑事的人一样,纵使安全向他招手,‘他却只顾向下看’。
在这里,故事必有一些‘窜改’。根据创世记十四章二节所清楚记载的,琐珥乃是亚伯拉罕时代的名叫比拉的城,而在形状和声音上都像希伯来语的‘小’字。它是平原上残存下来的惟一城市,所以很可能是罗得在灾难之后助长的。但是它之得以残存,是由于他的自私请求;而且作为一个异邦城市,说它自己取一个新名字形容它为‘小’,也是过份轻信了。那末,关于这‘小’字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是说故事者的杜撰。不过,无论如何却是一个很有效的添改,罗得的祈求与前章亚伯拉罕的高贵代祷对比,作者对他立意虽好却全是以自我中心,而且绝望地在优柔寡断的‘小’人之阴暗的色彩,加上最后的润笔。
我们要再一次指出新约未能全面把握旧约的要旨。希伯来书赞扬撒拉的信心,却简直忘记了她很坏很坏的暗笑。现在我们发现彼得在他的后书(彼后二7)论及 神搭救‘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得’。在这评语上,有一些真理,但是就全局而言,却是很紊乱的。罗得对他周围的一些事物不喜欢,但是他对其他事物却是喜欢的,而后些事物对他的影响要强烈得多。彼得如果留意创世记本身对所发生的事的意见:‘祂记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得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得从倾覆之中出来’(十九29)。就知道他的得救,并非因他自己的缘故,而是因亚伯拉罕的代求。
罗得不是我们的榜样。他声名狼籍的妻子也不是我们的榜样;而是一个警告。她‘回头一看’便灭亡了。当她有可能得救时,她还‘拖延’!作为人类,我们属于所多玛和蛾摩拉;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像罗得那样的‘迟疑’而又推搪呢?请参看马太福音六章廿一及廿四节;八章十九至廿二节。
判决(十九24-29)(续)
(十)
所多玛和蛾摩拉叙述方法正如旧约通常的情形,像是 神直接干预而发生的。但是与这故事有关的其他事件相比,这不是一个神迹──一个高龄女人生一个儿子才是一个‘神迹’。希伯来人可能视 神为这两件事的原动力,但是他们一定能以分辨非常的、但在自然或历史上可重复行出来的事件──诸如饥荒或战争的胜败──与非常的、因 神使其发生,而又透过它而达到特殊目的、只发生一次的事。
我们作这同样区别时,有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满心相信地谈论──而且谈论得蛮有意思地── 神在这两种事件里面或背后。但是惟有在第二种事件中,我们才趋于主张 神‘打破祂通常的定律’而行一个‘神迹’。对第一种我们避免用‘神迹’一词;我们通常不说‘耶和华将硫磺与火降下’的话。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期,知道这类的事有自然的原因和科学的解释。
说故事的人没有详尽地细述平原上的城市如何消灭;但是它给我们充分的数据,使所记载的与现代地质学,在高度矿物密度地区中,由于地震的或火山的活动产生的结果相一致。死海(希伯来人称为盐海)远在海平面之下,在其南面又没有天然的出口。其结果是含盐太多,不容任何水中生物存在;而其水中及周围地区有大量其他矿物质,如沥青和硫磺。这海由利山(Lisan)或‘舌头’──就是从东海岸延伸而来的半岛分割为两部分。在这海角上面,水深一千二百呎,但是在这角以下则非常浅。现在它大约是三十呎深。不过地质学家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它甚至更浅;而且死海的南段实在是比较挽近才形成的。
在本章我们必须回忆有关于这事如何发生的。十三章十节;十四章三节暗示约但谷没入西订谷,二者延伸远至琐珥,换句话说,死海当时还未存在。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死海浅低的部分尚未存在,而所谓‘平原的城邑’则在这个地区,当时称为‘西订谷’的则是它(参下图)。该地虽然‘有许多石漆坑’,却很肥沃(见十四10)。在主前第二十世纪初期或中期,一次地震或类似地震,使这些坑中的矿物质与天然气质着火,引起一次大爆炸,大火蔓延四五个城邑,只有最南的得以幸免。比拉或琐珥没有涉及。当那区恢复原状时,地面慢慢下沉,而死海的水则渐渐南移去掩盖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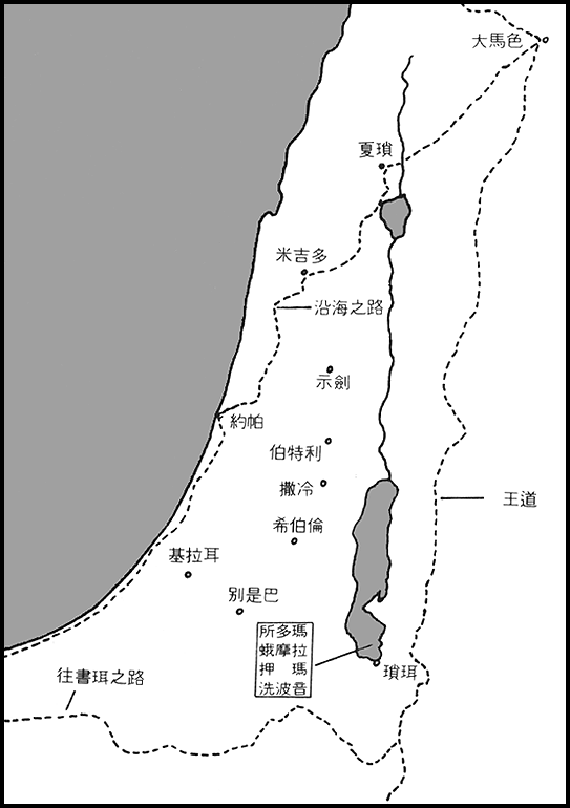
到大海之路
甚至对罗得妻子的死,也可以自然的说明处理。她在外面被掉下来的碎片所袭击,当场被焚,这便引致说她变成盐柱的故事。在今天的死海西南角有一个巨大的山脉,称为乌斯达姆山(Jebel Usdum亚拉伯文的‘司多姆山’),事实上大部分由石性盐柱所构成,而且经常自己破碎而又自己重新形成。以乎在这山脉上一个临时的突出或尖顶──在这情形它不能仍然立──活像一个女人的样子,也与这故事的想象相连系。
(十一)
不过,这故事给我们的教训,并非在于地质科学,乃在于 神,使我们与古代希伯来人同样相信,祂的手在这些可怕的事故后面。总之,平原上的腐败文化之消失,并非由于自然环境不寻常的一连串事故;而是因为它的邪恶使祂厌恶。在这里,警告是人人都清楚明白的。如果有人执迷不悟,则今天同样腐败的文化将重蹈覆辙──因为我们从自己所创造的可怕的核子武器,便都知道危险的存在。这一回, 神只要站在旁边一会儿,事故便会自己发生。
这警告也是对现代 神的百姓发出的。虽然他们像罗得一样,拖延推搪到最后一刻,他们仍然可以逃脱大灾难。但是如果他们像他的妻子那样越出了界限;如果他们在那最后一刻,‘回头一看’,他们便与其他的人类同归于尽。我主在论到祂降临时,凡想要保存生命却要丧失的人的典型时,提起她的行为(路十七32)。当祂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 神的国’时(路九62),祂心中也记起她的例子。
(十二)
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适当地和戏剧化地结束时,亚伯拉罕回到先前 神离开他之处(十八33),并且从高处往下望去,其时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而那里则是他侄儿曾建立家园之地。当他观看可怕的情景时,心中作何感想呢?说故事的人没有说,但是他加上自己的结论,说因为 神记念亚伯拉罕,罗得才得逃脱,确实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亚三2)。就这情形,至少他的代求是值得的。我们今天像亚伯拉罕为这危急存亡的世界祷告,或许不能救它脱离劫数──那要看 神的决定──但是我们可能救出少数人。但是如果我们‘回想罗得的妻子’──甚至加上罗得本人──我们自己可能正在那少数的人之内。
乱伦(十九30-38)
这使人惊讶的小段落,比九章二十至廿七节更使人惊讶!在那段里告诉我们,原来是洪水英雄的挪亚昏醉了,在他帐棚中赤着身子趴卧。含因为不够庄重没有避着这情景而受咒诅;而含的儿子迦南虽然不在场,却也一同被咒诅。这里罗得被女儿灌醉了,然后轮流与他同寝。这乱伦私通的子孙,被名为以色列东邻摩押与亚扪的祖先(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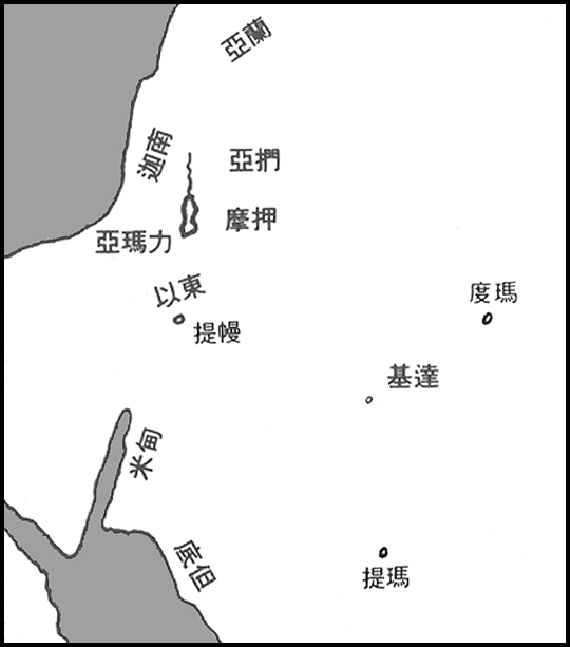
国民族
(一)
这故事与所多玛蛾摩拉的结束相连系。在那里罗得求天使饶恕琐珥,但是他现在却怕住在琐珥,逃去他曾经迫切要逃的那山。或许那‘小’琐珥的人把他赶走。总之,他曾放弃他的帐棚,去求一个漂亮的城市住宅(参十九3),如今却要逃入摩押人与亚扪人后来定居的死海东部高原中一个可怜的山洞去。言外之意是这山当时从没有人住过的。他的女儿们失掉她们的未婚夫,没法找到他人,以致引诱他犯了乱伦,好叫她们从他‘存留后裔’。在创世记和历史的记载消失之前,让我们对这悲剧性的卑污而又带讽刺的场面,作最后一瞥。
(二)
不过,我们感觉到,叙述者已经对罗得失掉兴趣,而在这些经节中比较关心的则是对摩押人和亚扪人的中伤。我们没有办法确知,罗得从希伯来传统之始,便与摩押及亚扪有关连(它不像以实玛利那样显然有种族上的关系);或者事实上由于前面说到他结果在死海东岸的琐珥的故事,引致作这样的联系。我想是后者。
但是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们或许不应把这段当作亚伯拉罕史诗的一个主要部分。正如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它给那追寻亚伯拉罕与他越轨而又迷误的侄儿的败坏关系的史诗之分段,补充一个恰当的大结局。但是它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说及以后长期以来,一直为希伯来所不喜欢的两个种族的起源,对它们说些不愉快的话(作为例子,参民廿五1-5)。我们应以处理对迦南的‘咒诅’(参看对这段落的注释──关于希伯来民族表的思想)之同样态度来处理它。作者希望他的读者把由乱伦而生的摩押人和亚扪人。与那沉入‘兽奸’的平原城邑列为同等。这并不是说 神曾经这样作,或者我们应当这样作的意思。──《每日研经丛书》